在电脑里发现了这篇“古老”的文章——古老到几乎都忘了。我查看了文档的属性,是2000年2月的。然后,打开文档,很多记忆就像附着在沉船上的贝壳一样,在幽暗的海水下面静静地呼吸着。
读刘小枫,还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几年。那是在一家私人书店里买了一本《走向十字架上的真》,虽然我对基督教一无所知,却完完全全被刘小枫笔下那些神学家的思想迷住了。我开始发现在自己熟悉的这个世界之外,还有另一个更加浩瀚和神秘,也更加迷惑和冲突的思想世界。
后来,我买了这本《沉重的肉身》,也因此对昆德拉、基斯洛夫斯基产生了永久的兴趣,并意识到那个浩瀚的思想世界,其实就附着在我们身边这个世界之上,就好像是终身没有离开小镇的康德。我开始用笔在一个又一个夜晚记下自己的感受。
在写作上,我并无天赋,但对思想的热爱,让我有勇气写作。直到今天,我从没有离开过那天在冬夜的台灯下写作的自己,那个活在狭窄的空间里却有着无限世界的自己。

赫拉克勒斯发现自己面临着选择,两个女人(卡吉娅、阿蕾特)都向他伸出手。他茫然无措,不知应该揽住谁的腰肢,到底哪一个才通向幸福之路,象征轻逸、享乐的卡吉娅,还是自称是神明的伴侣的阿蕾特(她将带来辛劳和沉重)。这一事件在鼎鼎大名的希腊哲人柏拉图叙述中,隐含了“你应该和阿蕾特在一起”的道德指令。二千多年的时间像流水一样渗进土地,道德的清规戒律已然不再具有话语特权,可刘小枫在重新考察了这个故事之后,还是告诉每一个寻找幸福的人,要和阿蕾特在一起,抓住神明的衣襟。
卡吉娅与阿蕾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女人,代表了两种迥异的身体感觉,在古代因道德原因而高高在上的阿蕾特,一直以极端的蔑视来看待追求享乐的卡吉娅,并命名卡吉娅为“邪恶”。而在现代语境中,阿蕾特不仅失去了道德特权,连与卡吉娅平等的地位也得不到,在现代西方,翻案、拯救的对象已不是卡吉娅,而是阿蕾特。刘小枫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对这个古老的故事进行考察的。
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体感觉都源于对幸福的追求,甚至幸福本身也就是某种身体感觉。卡吉娅的幸福即身体感觉的轻逸,阿蕾特的幸福即身体感觉的沉重。刘小枫没有仿效柏拉图,对不同的身体感觉加以道德评价,分别贴上“邪恶”、“美好”的标签。作为一个现代启蒙之后的哲学家,刘小枫承认了不同的身体感觉的平等,可他为什么又作出和“阿蕾特在一起”的结论呢?换句话说,他为什么再次替人们选择了“沉重的肉身”,却不去走一条轻松的生命道路。
其实,这样的选择问题在柏拉图的时代并不比现代艰难,相反倒简单的多,在当时的世俗以及精英头脑里的伦理体系中,阿蕾特先天就具有了纯洁、美好的品质,因此凌驾于卡吉娅之上,“赫拉克勒斯的故事”实质上是伦理教材。只有在现代的语言季候里,两个女人不再有价值上的高低之别,她们只是不同的但却是平等的身体感觉,如何选择才有作为问题提出的可能。
为什么要“和阿蕾特在一起”,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接受卡吉娅,那会有个什么样的结局。长于语言编织的刘小枫从昆拉德的手里,引来托马斯、萨宾娜与特丽莎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几乎是“赫拉克勒斯的故事”的现代翻版。托马斯,即赫拉克勒斯最先抱住的是萨宾娜(卡吉娅)丰盈的身体,相信“灵魂不过是附在身体上的一个语词”,“努力要在肉身的无差别中去探索肉身的差异”。然而,最终托马斯发现自己坠入了一个让身体毫无差异的境况。这个抹去每个个体生命的结局,正是托马斯最初要反抗的。在萨宾娜(卡吉娅)那里,灵魂和身体相互远离,身体放开手,灵魂飘上天空,没有灵魂的身体千篇一律,面目随意模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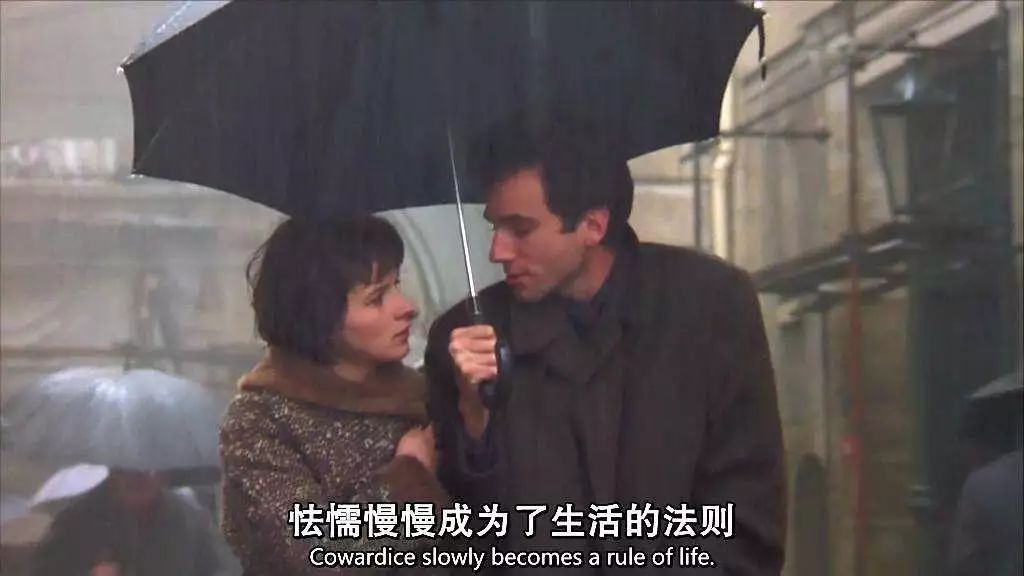
个体命运本是一连串的偶然,命运的乖谬、强大、无理、不可捉摸都因为每个生命都是一次偶然,“是亘古无双的唯一一次发生”,生命的意义全在于此。“身体的沉重来自于身体和灵魂仅仅一次的、不容错过的相逢”, 身体只有服从灵魂,才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呼吸。只有在特丽莎(阿蕾特)那里,身体和灵魂才能够聚合。生命因偶然而独特、而脆弱、而沉重。
“肉身不再沉重,是身体在现代之后的时代的厄运。身体轻飘起来,灵魂就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栖身处。”刘小枫并不能在暮霭沉沉的生存之路上为所有个体生命指路,他只能是打亮自己的思想,赶在黑夜来临之前,为自己的灵魂找一块栖身之地。
 资源分享网
资源分享网